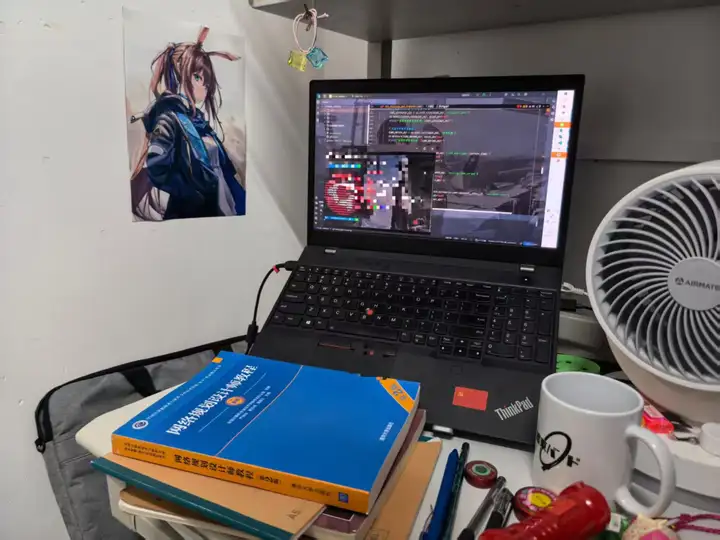芒星
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
理论上,它应带我从孤独中逃离。
我本该被迫与它寸步不离。
害怕它的影子继续纠缠,令我窒息。
如今我却仍坐在这里。
太阳在山路的那头被升起的山峰遮住了半轮。我轻轻走过青草穿插的石板小路,走上泥泞的大路。路两边的杂草依旧很多,我仔细地从路首找到与山下公路融为一体的路尾,依然不见那束花的踪迹。从那一次见过它后,我便再不可于这条路上找到它了。
就像它随着她一起消失了一般。
我慢慢坐在路堐上,双目有些迷茫地望着金色的太阳敛起光辉。
再不可知那花的名字。再不见你。不再。
我在那里埋下一栽小小的蒲公英。
那么一支渺小的花在山风与记忆里时隐时现。
与其说是为了纪念,倒不如说是为了忘却。
1
我似乎不太记得我为什么于此工作了。反正,从我有点记忆起,我就一直呆在站点,呆在于山,呆在寂秘的树林与那未收割过的麦田的交界处那栋小瓦屋里。不引人注目,这一设施上完美诠释了这一要求。看似破旧平凡的小瓦屋,实际上联控着深埋在山中的数个军需仓库与山顶天文台的所有安保措施。
我的工作,说好听点叫分站总负责人,说直白点就是看仓库的。人家至少还可以在闲暇时刷手机啥的,我一来上班,什么收发装置就都被没收了。每天那盏小小的警戒灯,永远是平静的绿色,我眼前的景色永远是一片望不到头的麦田与更远方的群山。当然,我被允许偶尔地出门走走透透气,但我不爱出门——透着窗子和不透着窗子看景色似乎没什么差,而小屋里有冬暖夏凉的空调。
虽然无聊,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从小到大都是——换句话说,我从来都是一个孤独的家伙。听过一个笑话吗?一个人总是乘小舟去河上钓鱼,但每次什么都没有钓到,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钓鱼了,但他依然每天早上去钓鱼——因为他喜欢的不是钓鱼,而是独坐孤舟无所事事。
所以这个工作很适合我。
01
每个人都在青春期时有玫瑰色的幻想。我也不例外,虽然住在闽侯大义这样一个在福州算偏远的地方的最偏远角落里一座大山上,但环绕我的群山阻碍不了我放飞的想象。我每天要走六公里的山路去大义中学上课,大约于我两个小时的路程。这一路上都是树林,林子里除了树连只鸟都没有,安静的很。这样的时候就很值得幻想。
幻想什么呢?
有一次在湖那里跳了下去。
水面很清,阳光透进来,浅蓝浅蓝的像天一样。但往下沉去,水底全都浸在黑色里,愈深愈浓的黑,水底就像没有似的,黑色的渊谷像一团浓墨聚在我脚底。我喘不过气,开始咳嗽。咳嗽了一股水流涌进鼻子,脑袋随着肚子一并发沉。
我口音很重,讲话老是平翘舌不分,声音又小,身边人总当我是空气。
我在那一刻沉下去。
水面清圆,蓝得让人有点炫目,但视野却在一点点黑下去。
孤来孤往了十三年。往下沉下去。
对我来说什么都像山林一样安静。林子里以前有活物的,都被打了去卖钱。太阳小小一轮悬在蓝天上,洒下来的光线在雾蒙蒙的树林间是有形的,我伸手去摸过,除了暖什么也感觉不到。光是没有一点分量的,轻,比羽毛都轻。虽然感觉不到实在的玩意儿,但我喜欢那些光柱,它们比实在的东西更让我喜欢。我喜欢光。我喜欢太阳。黑暗是无形的,但黑暗很有分量,重得一直把我往下拖。
我开始挣扎着往上游。
水面是天蓝色的,属于太阳。
而有光透过的地方总显得那么好。
02
光柱是片状的,暖洋洋,分明触摸不到它,但我觉着它一定是软乎乎的触感,可能比羊毛绒子摸起来软得更很。林子里很亮堂,充满了光亮,山谷就像一碗盛着花生油的黑瓷碗。
我躺在湖滩上睁着眼睛,忽然看见一抹明亮的光芒在眼前的枫树上摇曳着。
那是我头一回在林子里碰见活物。原来阳光是活的。
但那不是阳光。
她从枫下轻盈地走来,踏过地面上落满的层层干叶,但脚步却依旧悄然无声。与其说她在走,不如说她在飘动,就像被风托起的羽毛。待她近了,我看见她在笑。笑得像清圆透亮的水面,笑得像林间飞扬的柔光。
我没想过她会在这儿出现。正因我没想过,她不应该不可能在这出现。
我没想让她笑,但她笑着,眉眼弯弯。她笑起来的样子绝非我贫乏的想象可以形成的。
风转过湖面,凉凉地抚过我满身的伤痕,凉凉地吹起拥抱着的粼光,凉凉地摇下满树红叶,凉凉地卷起金黄色的长发飞舞。
我想起林间的阳光柱子被摇动的叶迷蒙的时候。那样的光片落在地上会泛出不同深浅的斑状金黄。
我意识到,她活了。
04
假的东西融不入真的世界,幻想的泡沫化在现实的熔炉中。
她已经变得很透明了。
有时候,我对着我的心房呼喊了好几声,她都不会出现。
她已经很脆弱。
我和她在林子里走着。阳光穿隙过叶缝,也穿隙过她的身体。
上学路上遇到的事物依旧会让她惊喜与好奇。在一个泥泞的雨后,大路两边有很多杂草挂着露珠于晴空下闪烁。她从这边跑到那边,从那边跑到这边,惊起两只蝴蝶珊珊飞起。我看着她的背影在我眼前逐渐远向地平线,忽然从心底感到一阵悸动。而这段哀伤我明白也不能长久,过个五年,十年,就连这样的回味都会消失。
我跟在她身后回答她的问题。小石子。牵牛花。狗尾草。两只轮子的叫脚踏车。水洼边上的是一只火蚁。水洼里边的?蓝天白云?还是那轮明亮的太阳?
她俯身凝望着水洼中平静的映像,忽然起身,但水面里的颜色没有一点变化。
她没有倒影。
除了在我心目中,她对于世界真的就只是一缕幻影。而总有一天,她将真正变成一名虚妄无形的存在。因为我不能永恒将其挂于心头。她会逐渐从我的心灵中消失,不论如何。
一杆弯曲的瘦茎,但结着的花却是白色的?只有那么一株低垂于湿沉的雨露中。从没见过这般的花,像雪般好看,但真的不认得。走吧,芒,我们要迟到了。
好看但不显眼,深埋于那丛杂草里。从那天开始我便再没见过那种花。随着时间走向路的尽头,花的样子我也慢慢忘却。而这时间不过是转了个弯的一刻而已。
再不可知那花的名字。但看那蓬松的花朵,应当像羽毛般轻。如果那时有阵山风吹来,那一扎白花会满天飞舞,景色会很漂亮的,对吧。
那样的话,也许我就会记得久一点——我只想记得久一点。
2
日子这般过下去确乎有些乏味。我向上级请求安排一个人和我一起工作。这样多一个人不影响摆烂还可以解解乏。那群人没同意,也许是鉴于站点的机密性。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站点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机密等级。我是总负责人,我明白这个庞大设施的完全情况:两个部分,军仓库与天文台,一个在山腰一个在山顶,而两部分的安保密钥都在我手上。前者是站点三成装备的存贮点,后者用于监视及观测天象类高空类异常活动,譬如“从天而降”,仅此而已,我可以肯定没有更多秘密了。而我觉着最不可理喻的是天文台选址是于山这个市中心小土包,这里交通发达吵的要命光污染更是严重,这样低的海拔看空中什么东西和在地面上直接看真没什么区别——所以为什么天文台不建鼓山顶上?
然而没必要想太多。好奇心真的可以害死人的。
03
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每一次我受了什么委屈,我掉下眼泪,她柔美的嗓音都会从我心底升起,轻轻愈合我内心的创痛。我长大了。高中。我所能达到的也只不过是那个大学,但这样的成绩在我这个高中也算极好的了。高三的生活繁忙得让人晕头转向。在这样繁重的学习压力下,我有好几天没叫她出现。周天晚上我终于得闲,于是我轻轻呼唤她一声。我轻柔的语言在心灵里流淌,在幽静的世间泛起空灵的回音,回荡,回荡。
但我的身边却依旧空无一物。
在?我又轻唤一声。
她慢吞吞地从台灯照不到的黑暗中走出来,我们没话找话聊了一会儿天就去睡觉了。
梦中也有一片安静的树林,我和她一步一步地于林荫间穿梭。每一个晚上,每一个一样的梦。她在梦中的双目有些哀怨,但只是一闪而过,让人不会在意的一闪而过。
你陪了我好久。对啊,你真的很好。……住在我心中,我的心不够广阔么?
你要去更大的地方?那我们还能见面吗?
……
不会的。不会这样。
消失?凭什么。凭什么一定要这样?
阳光不实在,但阳光是一切实在的源头。我喜欢阳光。她给我的温暖是实在的。林间没有小动物,因为这世上有枪,有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影子。影子是光给的,但却是实在的,像深湖里的水,很沉。阳光不实在。那朵花的花瓣也是,风一吹过来就会洒落满天,但,但那个时候没有风。
有风的话就好了。
有风的话,景色就会很漂亮,让人印象深刻,我就会对此记得久一点。记得久一点了,我就可以去知道那朵花的名字。我想再和她走过那条上学的泥泞路,想看湖边飞扬的枫林。我想去拥抱阳光,但阳光从我全身浸过暖意而永远不能让我触摸。我忽然想起,太阳离地球有很远很远,光都要走八分二十秒。
听说月光也是阳光的一种。而且,月亮离地球很近。
05
我想没人喜欢看玛丽苏。因为她们单薄,千篇一律,她们柔弱,死气沉沉。没有什么好去欣赏的。
她是玛丽苏吗?玛丽苏一定要长得美丽,性格温柔,善良到有点圣母心,唱歌要动听,举止也要可爱优雅,做事还永远笨手笨脚,而且,所有玛丽苏的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永远有人为她们付出,要么霸道总裁,要么有钱爸妈。总之,玛丽苏要幸福快乐地过一辈子。
如果她能成为玛丽苏就好了。她在那个世界可以幸福快乐过一辈子——在失去我后幸福快乐。
之后,在心底,在真实中,在我的愧疚与记忆里,我呼喊她。但她没有出现。我搁下键盘,从内心最僻静最隐洁的角落里,我听见她微弱而平静的一呼一吸。
不要忘却。
月光不是片状的,像轻纱一样摇曳。月亮比太阳柔和,不暖不冷,亮亮的,却不能给影子染上色彩。月光不实在,比阳光还不实在,但月光很美。我觉得白花在月下飞舞会比于阳光下更好看。会像雪,也可以像流星。
我也喜欢流星。
星光也不实在。而且它很远。但星光偶尔地可以流下泪,温柔其他万物不能温柔的宇宙。星星是眼睛。星星比月光和阳光都来得温柔。光是无声的。但星光道道下落无限时,夜空的弦音会响彻整座寰宇。如果这个时候,上学的路边吹过软软的山风,白花的花朵在一瞬间飞舞,摇曳的光洁与流星于黑夜中融为一体,那么那样的景色我会记得更久更久——直至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从未见过陨星的旖旎,我从未见过那白花若蒲公英飘然的样子。但我喜欢。我喜欢不实在的美丽。
但实在是,那天刚下过雨,一丝风也没有,我不记得花的样子,更不晓得花的名字。我,我除了她的颜色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她从我的迷幻中诞生,伴随我哭泣与辛酸的人生一并成长;她是我苦难里泛起的泪水与花的融合;她是我从小到大攥在手心里不放的一点萤火;她是我在混沌凌乱的万事万物中逼迫而出的娇弱百合……是我身后的游荡之影拥抱着一片清灵山风……是我不曾感受过的温暖在伤疤上的自我愈合……是,她是,她是烟火燃尽后在风中旋起的依依残烟,随着明亮的夜滑向不可预知的空间……她是我的星空,我的眼眸,我的长梦,我的诉说。她曾在嫣红色的枫叶雨中轻轻漫步,她曾在漫山遍野的月光里合眸唱歌,她曾在山谷的湖泊旁欣赏自己不存在的倒影,她曾欢笑,曾哭泣,曾一直在我身边编织着光的轻柔童话。
但她从来没有倾诉过自己的故事。
也许她没有故事。
走吧。
幸福快乐,不论何时。
你也要有自己的故事。
你是从我梦里走出来的么?既然天下终无不散的宴席,你为什么要来我的心中焕发生命?
为什么每天不一定能看见日出日落,但黑夜一定会降临?
为什么你的来历,你的过去,你的未来,你的归途,你的灵魂,你的梦想,我,我都无法去在这个世间为你掌握?
日出的时候,日落就是一定的。阳光,星光,月光放在很远很远的那里都是星光。宇宙有一百多亿光年的半径,温暖却只能以三十万公里每秒的速度传播。总会有世世代代无光的角落。
但总要话下去。
你知道吗?即使那时刮起了山风,花瓣也不会飞起。花朵沾了水,湿沉粘稠得像水底的渊谷。没有可能,便谈不上什么遗憾。
不论怎样,你都不会知道那花的名字。不会知道的。
爱了,来了,送那世界一片流星,走了。
对我而言,这真的就足够了。
3
安全灯变红了。就在一刹那。十分钟前我收到天文台那边传来的三级警报。威胁不来自于地面,而来自于深空。“从天而降",有意思。
本来我有机会随他们逃的,但我摆烂着睡着摆烂着醒了,威胁也就离我不到五百米远了。我思索着也逃不掉了索性接着躺着。在那一瞬间我还真有点佩服我自己摆烂到连命都摆掉。
我走出小屋,看着天空由黑紫转为刺目的金黄色。数十道十字流星以弧线快速向于山袭来。不知道从哪里刮来的山风,忽的一下掠过麦田,层层叠叠的麦浪卷起波澜,数支麦杆随着星落一并下降着飞舞。
天地间一片金黄色的绚烂星风。
警报等级在下降,下降到三级,四级,由红色变为橙色,因为大多金火流星正若烟火般快速消解。但警报又很快更尖锐地拉起——一级,灯变成闪烁的红紫色。有一颗半径三米大小的流星以二十米每秒的速度流过天空,向我直接而迅速地若雷电般刺来。同时,我手边的康德计数器数值开始快速崩塌瓦解,后来我得知,所有仓库里的设备与LDR稳定器全都报废了,整个广东省的时间都快了三秒钟。
但最后的降临不过为我的脸带来了一股凛冽的秋风。那颗流星的速度很快悠下来,最后悄声停在我面前。
满麦田汹涌的大风开始歇息,夜接着它千百万年的沉默不语。
光明一点点化为破碎的碎片消逝。
我终于第一次见过了她。
和善的微笑,金黄色的长发下于秋风中轻轻流苏。
像黑夜中落下的太阳。
像林间飞舞的柔光。
像清圆水面的粼粼。
像路边静息的蝴蝶。
像朝阳。像晚霞。
像星光和月亮暖起来的样子。
像是从二次元中走出来的人物。
一脸好奇无知而友好温柔地凝望着我。
而我愣了一下。
我第一步做的是和她拉开半米距离,第二步做的是用座机拨通中央区的紧急号码。
“这里是3号观察点,经度113.27, 纬度23.15,我是柊野,需要支援,立刻。”
我的一切幻想的她从天空而降。